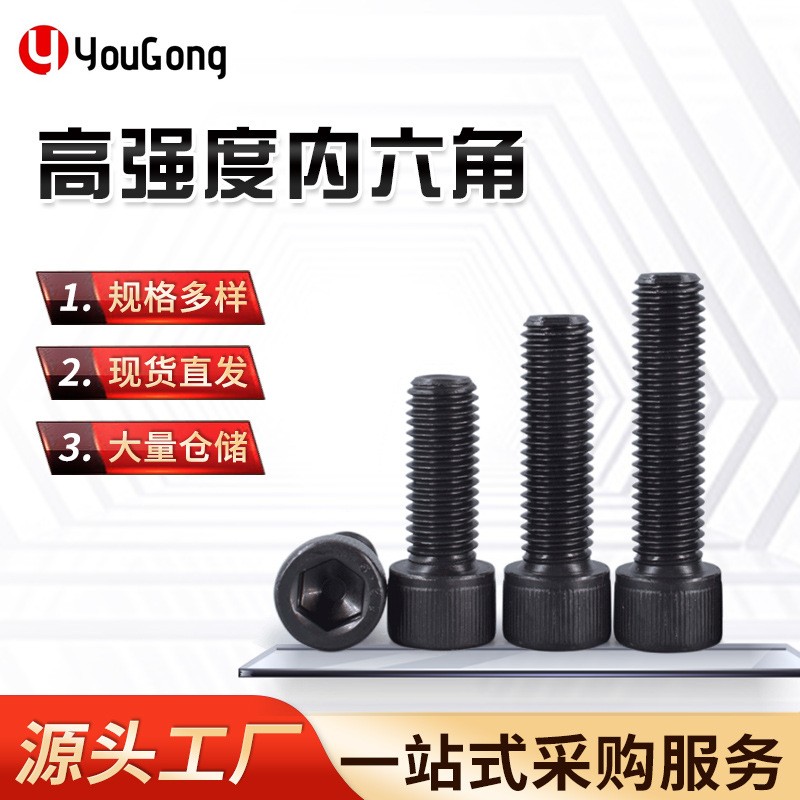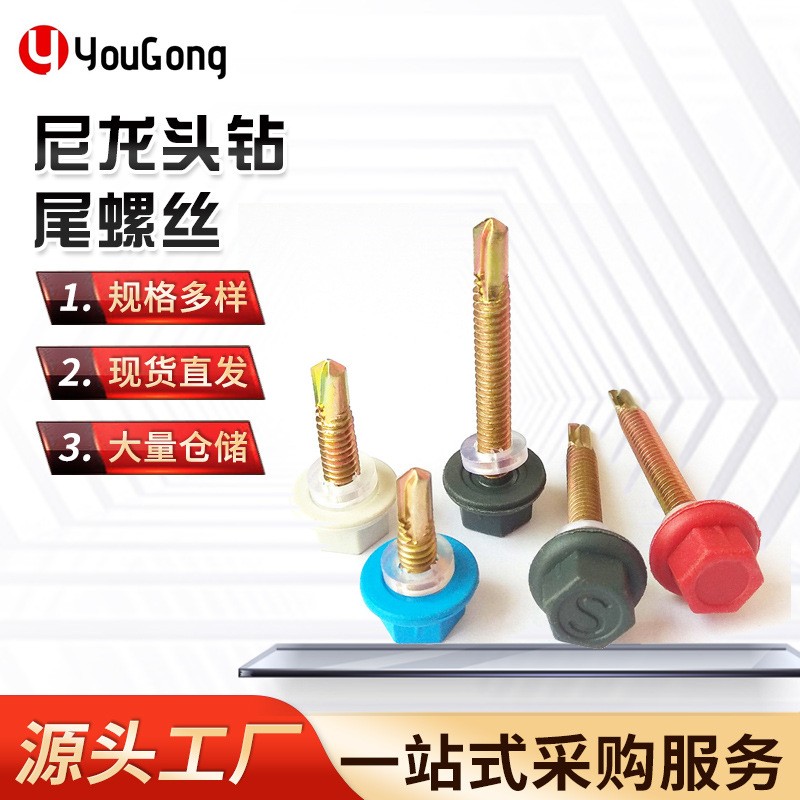在上海浦東的特斯拉超級工廠,每輛 Model 3 的底盤要擰入 127 顆螺栓 —— 這些螺栓的螺紋或光滑如鏡,或帶著細微的切削痕跡,卻共同支撐著整車 1600MPa 的碰撞安全標準;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,長征火箭的箭體連接螺栓,螺紋表面的金屬流線如水流般連續,它們要在 - 50℃到 60℃的溫差中保持密封,確保燃料不泄露;在山東某風電產業園,風機法蘭的連接螺栓,螺紋牙型帶著均勻的擠壓痕跡,要承受 20 年、上萬次的陣風載荷而不松動。

這些螺栓的 "牙痕",正是滾牙(滾絲)與車牙(車絲)工藝留下的制造印記。作為緊固件螺紋加工的兩大核心工藝,滾牙與車牙的競爭已持續百年:從蒸汽機時代的手工車牙,到流水線時代的滾牙量產,再到如今智能制造中的柔性選擇,兩種工藝的迭代不僅是技術進步的縮影,更藏著制造業 "效率與性能"" 標準化與個性化 ""成本與可靠" 的永恒博弈。
本文將跳出簡單的工藝對比,從材料科學、力學性能、制造場景、行業進化四個維度,拆解滾牙與車牙的底層邏輯:它們不是 "替代關系",而是制造業根據需求進化出的 "協同方案";不是 "誰優誰劣",而是不同制造場景下的 "最優解"。

滾牙(又稱滾絲)的本質,是通過金屬塑性變形實現螺紋成型 —— 就像用模具把面團壓出花紋,只是這里的 "面團" 是金屬棒料,"模具" 是滾牙輪(或搓絲板)。
在滾牙機的工作臺上,兩根平行的滾牙輪以相反方向旋轉,金屬棒料被送入兩輪之間。滾牙輪表面的牙型隨著旋轉擠壓棒料,棒料表層金屬在壓力作用下發生塑性流動:凸起的金屬被擠向牙頂,凹陷處的金屬被 "填滿" 牙底。整個過程中,材料既沒有增加,也沒有減少,只是從 "棒料形態" 變成了 "螺紋形態"—— 這就是滾牙 "無廢料成型" 的核心優勢。
從微觀上看,滾牙時金屬晶粒會沿著螺紋牙型發生 "定向滑移":原本沿棒料軸向排列的晶粒,在擠壓作用下向牙型兩側延伸,最終形成連續的 "金屬流線"。就像揉面團時面筋會順著揉捏方向形成連續的纖維,這些連續的流線能讓螺紋在受力時 "整體性承壓",而不是像被切斷的纖維那樣容易斷裂。
滾牙又可分為 "滾絲"(用圓柱形滾牙輪)和 "搓絲"(用平板狀搓絲板):滾絲適合加工長螺栓(螺紋長度可超過 100mm),搓絲則效率更高(單次可搓出成組螺栓)。但無論哪種形式,核心都是 "通過壓力讓材料自己 ' 長' 出螺紋"。

車牙(又稱車絲)的本質,是通過切削去除材料實現螺紋成型 —— 類似用刻刀在木頭上刻出紋路,只是這里的 "刻刀" 是螺紋車刀,"木頭" 是金屬棒料。
在數控車床上,螺紋車刀以特定角度(與螺紋牙型角匹配)接觸棒料,隨著主軸旋轉,刀具沿著棒料軸向移動,每旋轉一圈移動一個螺距的距離。刀具的刀刃會像 "鏟子" 一樣鏟下多余的金屬,形成螺紋的牙頂和牙底。被鏟下的金屬變成鐵屑,從螺紋表面脫離 —— 這就是車牙 "有廢料成型" 的典型特征。
從微觀上看,車牙時金屬晶粒會被刀具 "切斷":原本連續的金屬流線在切削處斷裂,螺紋表層會留下刀具劃過的 "切削痕跡",甚至可能出現微小的撕裂(尤其是塑性好的材料)。就像用刀切斷布條,切口處的纖維會散開,這些斷裂的流線會讓螺紋在受力時成為潛在的 "薄弱點"。
車牙根據刀具不同可分為 "螺紋車刀車削"(適合大直徑、非標螺紋)和 "絲錐攻絲"(適合小直徑內螺紋),但核心都是 "通過去除材料讓螺紋 ' 露' 出來"。

滾牙與車牙的本質差異,本質是 "力的作用方式" 與 "能量轉化形式" 的不同:
滾牙是 "靜壓力主導":滾牙輪對材料的壓力(可達 100-500MPa)作用時間長(通常 0.5-2 秒),能量主要轉化為材料的塑性變形能(約占 70%),少量轉化為摩擦熱能(30%)。這種緩慢的壓力作用,讓材料有足夠時間 "流動" 而不破裂。
車牙是 "剪切力主導":刀具刀刃對材料的剪切力(瞬時可達 1000MPa 以上)作用時間短(單次切削僅 0.01-0.1 秒),能量主要轉化為切削功(讓材料斷裂)和摩擦熱能(約占 60%),少量轉化為材料變形能(40%)。這種瞬時的剪切作用,會讓材料在斷裂中形成螺紋。
這種差異直接決定了兩種工藝的 "性格":滾牙依賴材料的 "順從性"(塑性),車牙依賴材料的 "脆性"(易切削);滾牙追求 "材料的整體性",車牙追求 "成型的靈活性"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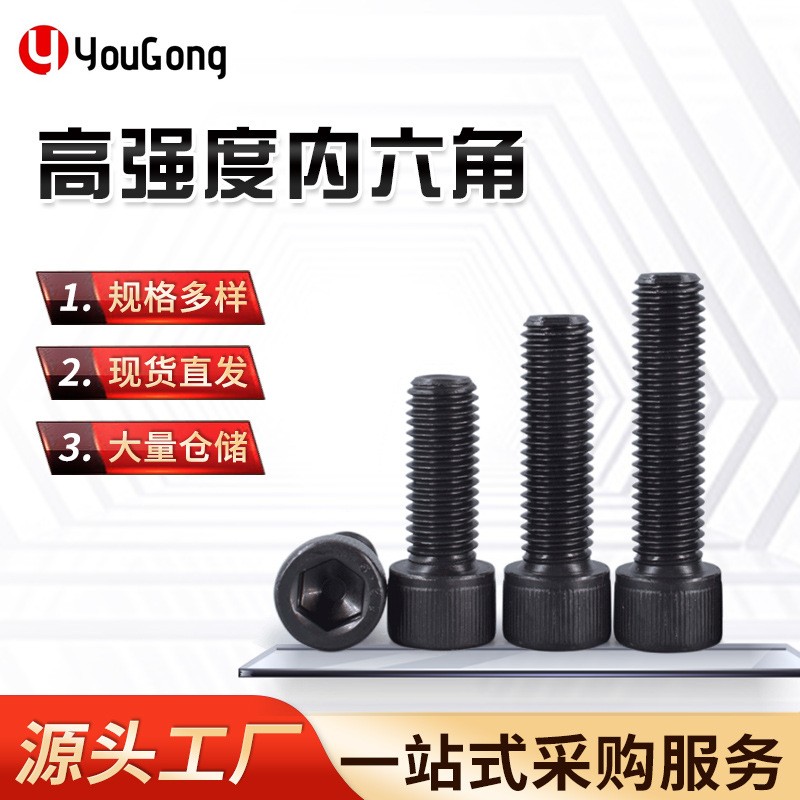
在某汽車螺栓工廠的質檢車間,工程師會用拉伸試驗機測試螺栓的斷后延伸率 —— 當數據顯示延伸率≥12% 時,這批 40Cr 合金鋼螺栓會被送入滾牙車間;若低于 12%,則可能轉用車牙。這 12% 的延伸率,正是滾牙對材料塑性的 "最低要求"。
塑性好的材料(如低碳鋼、合金鋼)之所以適合滾牙,核心在于其 "能變形、不變裂" 的特性:
從宏觀上看,這類材料在滾牙壓力下會發生 "均勻塑性變形",螺紋牙型能完整 "復制" 滾牙輪的形狀,不會出現裂紋;
從微觀上看,其內部晶粒有足夠的 "滑移空間",能隨著壓力定向排列,形成連續的金屬流線(而非斷裂);
從力學上看,塑性變形會讓材料發生 "加工硬化"—— 螺紋表層的晶粒被細化,硬度可提升 10%-30%(如 40Cr 滾牙后表面硬度可達 HV300,未滾牙時約 HV250)。
以汽車發動機缸蓋螺栓(材料為 45 鋼,延伸率 18%)為例:滾牙時,螺栓螺紋表層會形成 0.1-0.3mm 的硬化層,這層硬化層能抵抗螺母擰緊時的 "摩擦磨損",同時連續的流線能傳遞缸蓋的預緊力,避免螺紋滑絲。
在某機床廠的毛坯車間,球墨鑄鐵螺栓坯料被整齊堆放 —— 這些坯料的延伸率僅 2%-5%,若用滾牙加工,螺紋根部會出現肉眼難見的裂紋(用磁粉探傷可檢測到)。這就是脆性材料(如鑄鐵、高碳鋼)必須選擇車牙的核心原因。
脆性材料之所以不適合滾牙,根源在于其 "易斷裂、難變形" 的特性:
宏觀上,滾牙的壓力會讓材料發生 "非均勻變形",螺紋根部(應力集中處)會因無法承受塑性變形而開裂;
微觀上,其內部晶粒排列緊密(或存在石墨顆粒,如鑄鐵),缺乏滑移空間,壓力會導致晶粒間結合力斷裂;
力學上,脆性材料的抗拉強度遠低于抗壓強度(如球墨鑄鐵抗拉強度 300MPa,抗壓強度 900MPa),而滾牙時螺紋表層承受的拉應力可能超過其抗拉極限。
車牙則能避開這一問題:通過切削去除材料,無需材料發生塑性變形,只需刀具能 "切斷" 材料即可。以機床床身的鑄鐵地腳螺栓為例:車牙時,螺紋車刀會精準切去多余材料,雖然表面流線被切斷,但鑄鐵本身脆性大,受力時主要承受壓力(而非拉力),切斷的流線對其影響較小。

在某電子設備工廠,含鉛黃銅螺栓(用于防腐蝕連接)的加工車間里,永遠看不到滾牙機 —— 這類材料若用滾牙,螺紋表面會出現 "分層"(鉛層被擠壓后與基體分離),像樹皮剝落一樣。
含鉛材料(如鉛黃銅、含鉛鋼)必須選擇車牙,核心原因是鉛的 "低熔點、易分離" 特性:鉛在材料中以微小顆粒形式存在,滾牙的擠壓會讓鉛顆粒被壓成薄片,在螺紋表面形成分層,不僅影響外觀,更會降低螺紋強度(分層處易斷裂)。而車牙的切削能 "整體切除" 含鉛層,避免分層。
非金屬材料(如工程塑料、陶瓷)的選擇更簡單:塑料(如 PA66 + 玻纖)塑性較好時可用滾牙(需專用塑料滾牙輪),但陶瓷這類完全脆性的材料,只能用車牙(用金剛石刀具低速切削)。
隨著材料改性技術的發展,滾牙與車牙的材料邊界正在模糊:
對脆性材料(如鑄鐵),通過 "等溫退火" 提高其延伸率(從 2% 提升到 8%),可適應低速滾牙;
對高硬度材料(如淬火鋼,HRC45),通過 "表面軟化處理"(局部加熱到 Ac1 溫度),可降低滾牙時的開裂風險;
對塑性材料(如低碳鋼),通過 "滲碳淬火" 提高表層硬度,可減少車牙時的 "黏刀" 問題。
某風電螺栓企業的實踐顯示:經表面軟化的 42CrMo 螺栓(原硬度 HRC38),滾牙合格率從 65% 提升到 92%,這意味著材料科學正在讓工藝有了更多選擇。
在某航空材料實驗室的顯微鏡下,滾牙螺栓與車牙螺栓的金屬流線圖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形態:
這種流線差異,是兩種工藝性能差異的 "根源":
某第三方檢測機構對同材料(40Cr)、同規格(M12×1.75)螺栓的測試數據(樣本量 100 件),直觀呈現了性能差異:
在實際工況中,這種差異被放大:
汽車底盤螺栓(承受交變載荷):滾牙螺栓的疲勞壽命比車牙高 50% 以上,某車企的路試顯示,車牙螺栓在 20 萬公里后有 3% 出現螺紋裂紋,滾牙螺栓則為 0;
風電法蘭螺栓(承受預緊力 + 振動):滾牙螺栓的預緊力保持率(1 年后)達 90%,車牙螺栓約 82%(螺紋變形略大);
核電設備螺栓(高溫高壓):滾牙螺栓的應力腐蝕開裂風險比車牙低 40%(連續流線阻礙裂紋擴展)。

在某精密機床廠,絲杠螺母的連接螺栓(高精度梯形螺紋)必須用車牙 —— 這類螺栓不追求高強度,而追求 "螺距精度"(誤差≤0.01mm/300mm)。
車牙雖然在強度上有劣勢,但通過 "高精度切削 + 后續研磨",可實現滾牙難以達到的精度:
螺距精度:車牙通過數控系統可控制螺距累積誤差≤0.005mm/1000mm,滾牙受滾牙輪磨損影響,誤差通常≥0.01mm;
牙型精度:車牙可通過修磨刀具實現非標準牙型(如變牙型角螺紋),滾牙則受限于滾牙輪形狀;
表面精度:車牙后經螺紋磨削,表面粗糙度可達 Ra0.4μm(滾牙通常 Ra1.6μm),適合高精度配合。
在精密儀器(如半導體光刻機)中,這類高精度車牙螺栓是不可替代的 —— 它們不需要承受大載荷,卻需要 "零間隙" 的配合精度。
在某汽車緊固件工廠的生產線上,滾牙機與車床的效率差距肉眼可見:
這種差距的核心是 "加工原理":滾牙是 "一次成型"(螺紋全長同時擠壓),車牙是 "逐牙切削"(螺紋全長需逐圈加工)。對長螺栓(如 L≥100mm),滾牙效率是車牙的 10-20 倍。
但在小批量場景(如加工 10 件非標螺栓),車牙反而更快:滾牙需要 30 分鐘調試滾牙輪,車牙只需 5 分鐘編程,整體耗時(調試 + 加工)車牙更短(40 分鐘 vs50 分鐘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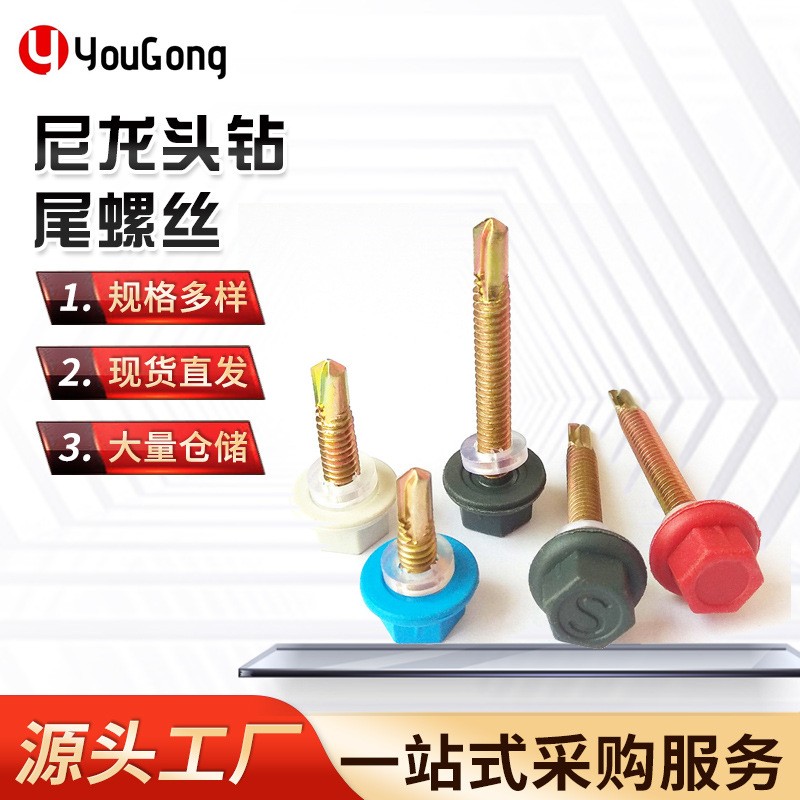
某緊固件企業的成本核算表(年產 100 萬件 M12 螺栓)顯示:
但對小批量(年產 1 萬件),車牙成本反而低 20%(滾牙模具分攤成本太高)。
全生命周期成本(含使用階段)的差距更大:在風電項目中,滾牙螺栓因壽命長(20 年無更換),全周期成本比車牙(15 年需更換)低 35%。
汽車行業對緊固件的需求是 "大批量、高可靠、低成本",這與滾牙的特性完美匹配:
乘用車:底盤、發動機的標準螺栓(如 M6-M20)90% 用滾牙,某車企的 BOM 表顯示,滾牙螺栓比車牙每年節省材料成本 1200 萬元;
商用車:重型卡車的大直徑螺栓(如 M24-M30),因批量仍較大(單車型年產 5 萬臺),多采用 "熱滾牙"(加熱后提高材料塑性);
新能源車:電池包螺栓(需防松)用滾牙 + 涂膠,滾牙的連續流線能保證涂膠均勻(車牙的切削痕跡易導致膠層不均)。
只有兩類螺栓用車牙:變速箱的異形螺紋(如梯形螺紋)、高硬度螺栓(如淬火后 HRC40 的半軸螺栓)。
在航空航天領域,緊固件的選擇邏輯是 "性能第一,成本第二":
火箭箭體螺栓(承受軸向力):用滾牙(30CrMnSiA 鋼),連續流線能抵抗 1000MPa 以上的預緊力;
飛機起落架螺栓(承受交變載荷):用滾牙 + 螺紋磨削,疲勞壽命比車牙高 75%;
發動機機匣螺栓(高溫高壓):用 "滾牙預成型 + 車牙精修",既保留流線,又保證精度。
車牙則用于:座艙內的裝飾性螺栓(小批量、非標)、鈦合金異形螺栓(鈦合金滾牙易粘刀,車牙更穩定)。
機床與重型機械的緊固件選擇,體現了 "按需選擇" 的實用主義:
普通機床:進給絲杠的梯形螺紋(大導程)用車牙(需高精度),固定螺栓用滾牙;
軋鋼機:牌坊連接螺栓(直徑≥M50)用車牙(滾牙設備受限),輥道固定螺栓用滾牙;
起重機:吊鉤螺栓(承受沖擊載荷)用滾牙(抗疲勞),卷筒端蓋螺栓用車牙(小批量)。
在某智能工廠的 MES 系統里,緊固件加工工藝的選擇已由 AI 決定:輸入螺栓規格、材料、批量、性能要求,系統會自動推薦工藝(滾牙 / 車牙 / 混合),并給出成本和周期預估。
智能化正在改變工藝選擇邏輯:
自適應滾牙:通過傳感器實時監測滾牙壓力,自動調整參數(如進給速度),讓脆性材料也能穩定滾牙;
數字孿生車牙:在虛擬空間模擬切削過程,提前優化刀具路徑,減少車牙的廢品率;
混合工藝:對大直徑螺栓,用 "滾牙預成型 + 車牙精修",兼顧效率與精度。
滾牙與車牙的競爭,本質是制造需求的 "鏡像反映":當工業革命需要標準化零件(如蒸汽機螺栓),車牙(手工→機械)滿足了 "能做出螺紋" 的基本需求;當流水線生產(福特 T 型車)需要 "大批量、低成本",滾牙的效率優勢凸顯;當高端制造(航天、核電)需要 "高可靠",滾牙的性能優勢成為關鍵;當定制化生產(智能裝備)需要 "柔性",車牙的靈活性再次被重視。
兩種工藝從未相互替代,而是像 "左右手"—— 右手(滾牙)擅長重復、高效的工作,左手(車牙)擅長精細、靈活的操作,共同支撐起緊固件制造的全場景。
隨著制造技術的進步,滾牙與車牙的邊界會越來越模糊,但核心邏輯不變:
對 "標準化、大批量、長壽命" 的緊固件,滾牙仍是最優解;
對 "非標準、小批量、高精度" 的緊固件,車牙不可替代;
對 "高性能 + 高精度" 的緊固件,混合工藝(滾牙 + 車牙)會成為主流。

就像人類制造工具的歷史:從石器到青銅器,不是前者被淘汰,而是各自找到更適配的場景。滾牙與車牙的故事,也是如此 —— 它們的競爭與協同,推動著緊固件制造向 "更高效率、更高性能、更高柔性" 進化。
在浙江某緊固件產業園的展廳里,陳列著兩顆螺栓:一顆是 1980 年的車牙螺栓(表面粗糙,卻支撐了中國第一條彩電生產線),一顆是 2023 年的滾牙螺栓(精度達 6g 級,用于 C919 大飛機)。這兩顆螺栓的 "牙痕",記錄著中國制造業從 "能造" 到 "造精" 的躍遷。
滾牙與車牙的選擇,從來不是技術的勝負,而是制造理念的體現 —— 是對 "需求" 的尊重,對 "平衡" 的追求。未來,隨著智能制造的深入,或許會有新的螺紋加工工藝出現,但滾牙與車牙留下的制造智慧(如何讓工藝適配需求),將永遠是制造業的核心密碼。
一顆小小的螺栓,螺紋上的每一道痕跡,都是制造文明的年輪。